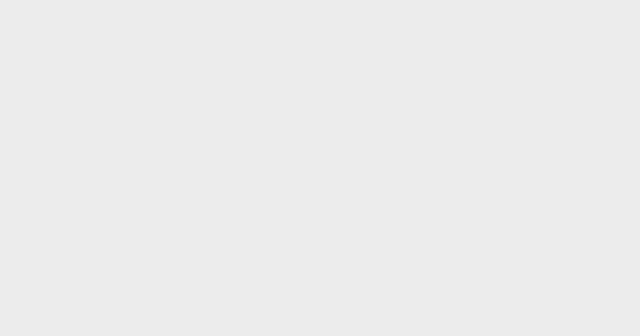「我們不是想太多,只是生病了」《我在精神病院抗憂鬱》給你與憂鬱和平共存的勇氣
「我是從煉獄裡爬出來的人,我有義務告訴世間地獄的模樣。」在一系列病發、懷疑、確診、病重、自殺、送醫等事件後,一直以來給人陽光開朗形象的左燈,被爸媽和醫師連哄帶騙送進精神病院,而促使她完成這本「微笑憂鬱症患者的住院日記」,紀錄親朋好友的真實反應和一路上的深刻人生體悟,不只為精神病院、精障朋友去汙名化,也讓有同樣歷程的你,能從她的故事中學習如何與精神病和平共處。

 - Rookie.jpg)
曾經有一度,我研究每個人的行為模式和興趣喜好,只是為了讓所有人都喜歡我。一路走來,也有人目光如炬,戳破我虛假的皮囊:「你超假。」─往往我會狼狽地落荒而逃。
我對每個人笑盈盈、曲意逢迎、虛與委蛇,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待人處世之道,說來諷刺,我還一度為自己深諳此道而得意洋洋。我想:眾生皆虛偽,我只是選擇了比較體面的虛偽之道。對於這種怪異的心理,我也曾經迷惘,但最後,簡簡單單的一句「人嘛,都有黑暗面」便足以消解。
同時,我堅信,一旦有人沒事找事,致力於闖進我的世界,剖析我的人格,他們會驚呼我如此做作,訝異於我深不見底的黑暗,然後毅然決然地離開我。
「一旦知道了真正的我是怎樣的人,他們就會離開我。」
─很可笑對不對?但這樣的桎梏整整束縛我二十餘年。
我是一個怪胎,這是我對自己最中肯的評價。「為什麼我這麼奇怪?為什麼就我一個人這麼奇怪??」
所幸,現在我明白,我的這種「心理殘疾」還有個專有名詞:微笑型憂鬱症。
像漂流了20 多年的心終於有了歸屬:我不是怪胎,我只是有病。─真的,這讓我欣喜不已。
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,憂鬱症就是「不開心」。但其實,持續的情緒低落只是冰山一角。憂鬱症最可怕的,是無法控制的身體機能退化,還有無法控制的認知思維改變。回溯過往,細細想來,病症其實很早就給了我「通知函」。
大約是2017 年9 月,我開始沒由來地對身邊所有事物喪失興趣,包括熱愛的音樂、電影、書籍等。走進電影院像是上墳,音響覆上了細細的一層灰塵,木心的詩集也長久地停留在同一頁。就是覺得沒意思。莫名其妙地覺得沒意思。起初以為是天氣變化引發的倦怠,就沒有在意。
後來,身體機能開始明顯退化。胸疼、頭疼開始侵襲,嚴重的時候我只能自捶胸口;記憶力、思維明顯減退,拿著眉筆找眉筆,一天到晚都在找手機;行動力變慢,如果別人的生活是流暢的畫面,我簡直就是以三分之一的速度播放;打翻水杯,打翻飯碗,成了一種常態;有些時候,會莫名流淚,但是你完全不懂自己在哭什麼;更多時候,你就是發呆,無意義地浪費著無意義的時間。
人變得非常非常疲累,一開始我晚上10 點睡,後來晚上8點就睡,再後來我下班回家7 點就能入睡。即便這麼長的睡眠時間,我依然覺得疲倦不堪,每天都感受著「身體被掏空」的無力,每天都覺得被人持續暴打了一頓。說一句話都感覺用了一輩子的力氣。能量像完全被榨乾了。以前用一分力氣可以完美地做好一件事,現在動用全身的能量,卻只能吐出兩個字。
網路上廣泛地流傳著一句話,可能可以解釋憂鬱症,為真正的憂鬱症正名:憂鬱症的反面不是「快樂」,而是「活力」。
憂鬱最折磨你的,還有你無法控制地質疑所有事物的意義。
從早上睜眼開始,你就開始做一份「考卷」,所有的問題格式是清一色的「為什麼要xxx ?有意義嗎?」:
─為什麼要醒來?有意義嗎?
─為什麼要起床?有意義嗎?
─為什麼要穿衣服?有意義嗎?
這種無意義的對意義的質疑,可以一直持續到你躺上床,跳出最後一問─為什麼要睡覺?有意義嗎?才能落幕。
在無數尋求意義的質疑中,整個世界都變得迷濛了,像是真的,又像是夢⋯⋯就是老隔著一層透明的薄紗,讓你看不清楚,摸不真切。總是莫名其妙地想倒下,卻每分每秒都被某些黏稠又有力的絲線拖著走。光天化日之下,歡聲笑語中,你卻在想著怎麼結束這一切。
很妙,這種被全世界隔離的感覺。任憑誰,對你做什麼,你體會到的都是一種隔靴搔癢般的無力感。
我決心試著與我的憂鬱症「和平共處」,為此,我還親切地給它取了個名字─「Mario」。聽說,只要給事物取名,就會產生羈絆與感情。我想,我要做好與Mario 如影隨形、共度一生的打算。
我非常想強調一下這段話,因為我想說,我在面對我的Mario 時,或者你們在面對你們的「Mario」時,請耐心點,再耐心一點。
它就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任性小孩,喜歡在不合時宜的場合調皮搗蛋。但它能夠教會你隱忍,教會你勇敢,教會你抗爭,教會你怎樣去生活,怎樣去面對慘澹的人生,它會帶你接近生活的真相。
正視它,接受它,並試著感謝它,再與它和解,並與自己和解。
我明白,這段話對於深受其害,被它折磨得體無完膚的你們來說,真的「大言不慚」。但是我的親身經歷證明了:我可以,即便我懦弱、悲觀、無能。所以,你也可以。
真的,卯足了耐心等待它安靜的一天。這一天,往往突如其來。或許是某個清爽的淩晨,或者是某個迷濛的傍晚,抑或是某個昏沉的深夜。它彷彿給你準備驚喜一般地和你握手言和。
我的Mario,餘生多指教呀!

病院裡的娛樂不多,當然事實上,絕大多數的病友也對所謂的娛樂毫無興趣。大多數時間都是這樣的畫面:一間病房,三個人,呆呆的,發著呆。這樣寂靜又可笑的畫面可以一直持續到廣播叫大家去吃飯、跳早操或者接受治療。
串門子成了最重要的日常活動之一。
我們病區全部的活動範圍就是一條走廊加一個大廳。所有進出的門都被鎖死。所以每個人看著每個人都面熟,甚至很多人都成了並肩抗病的摯友。我情況好一點時,就往病院的「大通鋪」跑。因為我進來的時候沒有病房,就睡在十幾個人一間的「大通鋪」,一下午呼朋引伴,認識了好多朋友。
可能很多人覺得,精神病人難以理喻甚至有點可怕,但我後來慢慢發現,在精神上有障礙的人,往往都是不願意傷害別人,而寧願選擇傷害自己的人,他們都是溫暖而善良的好人。
我相信,如果一個正常人參與我們的日常聊天,他一定會覺得駭人聽聞。
我們湊在一起,展示著結束生命時的各種傷口,嘴裡輕描淡寫地說著:「你是什麼病啊?」「你是怎麼自殺的啊?」「不要割腕,會有疤,你看。」「我吞了一整盒藥呢!」「我不後悔當時跳樓的決定。」─像是大家剛好在菜市場買菜時遇到了,閒話家常般地討論著「重於泰山,輕於鴻毛」的生命。
其實,我們對「命」這個浮華的東西棄之如敝屣,就連互相鼓勵的話也都是「活著啊好朋友!」這樣無力的訴求。但是,我們是真心誠意地希望這句話能說服對方「活著」,但心裡明白,這句話始終勸服不了自己活著,所以也是真心誠意地希望自己「能走」現在,我這樣平靜地敘述著,甚至還覺得我們就像是當年頹喪的「非主流」們的大集結。但其實我們都懂,彼此內心的曲折究竟是有多曲折。
最後小浣熊說:「死了一定比現在活著好。」我想力挽狂瀾,強撐起精神說:「當時死了也就死了!但我們現在活著,那就只能活著!」
小浣熊說:「沒有第二種選擇了嗎?」
我堅定地回應:「是的。」
然後心裡想著:死了比現在活著好。一定的啊!
直到現在,還會有人問我:「你當時到底怎麼想的?」
而我的回答也永遠都是:「我不知道,我被控制了。」
我、被、控、制、了。
從一顆一顆取出藥丸,在掌心收集,一次放進嘴裡,到最後喉嚨滾動吞下去。這樣一氣呵成的動作,是有人在「指揮」我。
真的。他用半死不活又亢奮陰險的聲音蠱惑我:「吃下去,你就自由了!你就自由了!!」像上演著一場萬劫不復的魔咒。
而我要自由。─這就是我自殺的原因。


短暫的生日宴結束後,朋友們要走了。
在病房裡,我最好的朋友輕輕地跟我說:「你沒發現你現在已經融入他們了嗎?你跟他們走得太近了。」我沉默。
她說:「你總得要重新融入社會吧,你給你媽媽帶來多大負擔啊!」
我跪倒在椅子上,語帶哽咽地說道:「我也想繼續工作啊!我也不想給家裡人帶來負擔啊!」可能突然被自己感動了,我真的啜泣哭了起來。另一位朋友拿了衛生紙給我,我好朋友看我這麼扶不起也怒上心頭,說道:「你別管她,隨她哭!」
於是,我最後一根神經「啪啦」一聲斷了。我異常激動地對著她吼:「為什麼要這樣?!」然後起身狂奔跑到大廳去找我媽,像一個受了欺負跑去跟媽媽告狀的孩子。
當時是吃飯時間,大家都在大廳吃飯。我「撲通」一下撲倒在我媽懷裡,不顧他人地大聲尖叫,放聲大哭。我的嗓音真是好啊,我覺得我飆出了人間難得一聞的海豚音。我媽被我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壞了,緊抱著我緊張地問到底怎麼了。整個餐廳的人也驚呆了,紛紛過來詢問狀況。我什麼都管不了了,只顧著自己飆海豚音。這就是我的名氣在病區一炮打響的開端。
意識到我開始失控以後,我越發絕望。控制不住的情緒爆發,意味著我過去二十餘年打造的「冷面笑匠」的「人設」開始崩塌。在其他人面前,我希望我自己永遠是理智的、平緩的、深藏不露的、波瀾不驚的。但現在,朋友隨隨便便的一句玩笑,對我來說,都足以致命。
我接到了我好友從北部打來的電話。她說聽了來看我的朋友的描述,覺得我身處的環境很可怕。什麼「姐姐」「弟弟」什麼的,他只希望我趕快出院回家。
在我眼裡,他們是最能理解我的病友,是一起並肩作戰的朋友。而在我的朋友們眼裡,除了我,他們都是神經病。但我覺得她們還沒明白過來,我也是神經病的事實。
好友繼續說:「『我們』正常人不能待在裡面。」
我回:「是『你們』正常人不能待在裡面。」
好友固執地糾正:「是『我們』正常人!」
我堅持劃清界限:「是『你們』正常人。」
意識到朋友對我的殺傷力,我開始重新審視我與朋友們的關係。我清楚地感覺到:他們根本無法理解。
確實如此,有時候,我自己都不懂自己。這種強烈的隔閡感很奇妙。比如,你昨天吃了蛋糕,即便你今天吃了雞腿,你也能記得昨天蛋糕的味道。但若你今天狀態好一點,你就完全無法理解昨天為什麼一心求死。
所以,每當朋友們真心誠意地說著「堅強點」「會好的」「想開點」「振作起來」時,都讓我在心裡更確認這件事:這場戰鬥,註定要我一個人孤軍奮戰了。
因為世界上,沒有感同身受這種事。


回到病房,我爸佯裝高興地和我說著話。但我不知道怎麼面對他。
我心裡明白,他在竭盡全力支撐這個殘破的家。養子債臺高築,解除關係又面臨重重考慮;女兒患精神病住院,情況反反覆覆;妻子的心情無法消解,精神幾近崩潰。但他不能倒下,作為一家之主,丈夫,父親,男人。但其實,他也就是個一心維護著家庭的普通人。
我覺得我實在不夠優秀,我的存在,就是為了給這個家庭蒙上更深的陰影。現在我生了這種病,更是給父母帶來太多麻煩,太多不安,太多桎梏。在黑暗中,我淚眼婆娑地盯著我爸的眼睛,艱難地吐字:
「你⋯⋯」
「是⋯⋯不是⋯⋯是不是⋯⋯」
「很⋯⋯很⋯⋯後悔⋯⋯」
「很後悔⋯⋯」
「生⋯⋯了⋯⋯我⋯⋯」
你是不是很後悔生了我。
─這真的是我二十多年的疑惑和心結。
我爸明顯被我的這個問題嚇到了。他驚覺,他乖巧伶俐的女兒,竟然有這樣不祥的心理活動。他堅定地說:「不後悔。我也絕不會後悔。二十多年,你從來沒讓家裡人擔心過,也沒麻煩過家裡人一點。你會得這個病,就是因為你實在太乖了。」
我淚如泉湧,慌忙道歉:「對不起!對不起!我從小到大,做的一切努力,都是為了讓你和媽媽能開心一點⋯⋯我希望自己成績卓越、功成名就,至少能給你們帶來一點安慰,哪怕一點也好。可我現在在這裡!可我現在卻在這裡!我不該得這種病的!都怪我!⋯⋯」我邊哭邊嘰哩呱啦、語無倫次地講了一大堆,最
後一句話是:「我覺得,沒有我,大家會過得更好⋯⋯」
我爸回:「我不需要你功成名就,我不需要你做高官要職,不需要你做到才華橫溢,不需要你做到出類拔萃,你什麼都不用做,你就做我的女兒。」
─他是我爸爸,一個庸庸碌碌的普通人,卻是我最偉大、最強大的父親。
都說父愛如山,我爸這座大山更是緘默。但為了治癒我,他把這輩子的噁心話都說盡了,天天「愛愛愛」的,什麼「我無法失去你」「你是我們的支柱」「你永遠是我女兒」「爸爸很愛很愛你」的話,都說了個遍。
在憂鬱症治療的過程中,家人的支持和理解舉足輕重,可以說是渡過這個難關最重要的一把鑰匙。我爸為了我,苦苦鑽研憂鬱症,包括形成機制、軀體表現、康復手段等。硬是從一個精神科門外漢變成了半個專家。說起憂鬱症來有模有樣,還能向別人普及知識、說道半天。
他監督我按時吃藥,在我痛苦時盡力勸解,最讓我安慰的是:他明白這是一種病,是生病的大腦在向我發出錯誤的指令,而不是我自己在沒事找事,無病呻吟。
我真的為一些憂鬱症患者感到心疼,特別是當他們至親的人,尤其是父母,說出「你這不是病,你就是太閒,你太脆弱了」這樣不負責任的話的時候。
這該是怎樣的感覺啊。像是被欺負得遍體鱗傷的小孩回到家裡,希望得到一點安撫,爸媽卻一邊向傷口撒鹽一邊說:「還不是你自己造的,撒點鹽就好了。」
外界的波濤已是如此洶湧,停避的港灣又是如此殘破不堪。
讓他們怎麼孤注一擲地去面對這一切呢?
我很慶幸,有這樣一位父親,也很慶幸,有竭盡全力去理解和支援我的家人。Mario 給了我一次重新審視人生的機會,也讓我真切地明白:什麼叫作真正的家人。

書名:《我在精神病院抗憂鬱:我們不是想太多,只是生病了,一個微笑憂鬱症患者的住院日記》
作者:左燈
出版社:三采文化
Source:Pinterest, 品牌提供
-
By 台灣女生日常編輯部
追蹤IG帳號:girlstyle.tw